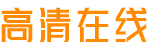播出平臺從愛奇藝更換為騰訊視頻,名稱從原來的《一年一度喜劇大賽》更名為《喜人奇妙夜》,對于米未這檔重磅的喜劇綜藝來說,也不失為一個全新的開始,畢竟兩年前的《一年一度喜劇大賽2》已經招致不少批評,不論口碑、出圈程度還是影響力都弱于第一季。
從第一賽段的20進15來看,《喜人奇妙夜》總體獲得不錯的口碑,它更多延續《一年一度喜劇大賽》的基因,主打“素描喜劇”,即,sketch,利用素描喜劇的輕便、明快、靈活、創新等優點,砸掉一堵舊墻,“解構”以小品為代表的傳統喜劇的種種框架和束縛,為觀眾帶來笑聲。

兩期過后,《喜人奇妙夜》熱度不錯
只不過,節目提到米未是“喜劇地獄”,每個參加節目的人都被磨得非常痛苦。痛苦源于節目不知不覺間將素描喜劇小品化:追求完整的起承轉合,結尾上價值,喜頭悲尾……當喜劇創作者以創作春晚小品的狀態不斷打磨一個素描喜劇時,固然體現了精品化的追求,無形中也重筑了一堵新墻。喜劇創作不該是只能如此痛苦的事情。
砸掉舊墻
何為素描喜劇?《一年一度喜劇大賽》專門為大家做了科普,直接援引當時節目組打出的介紹:“什么是sketch(素描喜劇)呢?它和我們所謂傳統的小品區別性的地方在于,它非常簡短,所以,它基本上只專注玩一件事,就是那個‘游戲點’,‘游戲點’基本上起源于生活的情緒,一旦捕捉到了這個好玩的游戲點之后,怎么玩?就是通過不斷地升級。”
《喜人奇妙夜》的多數作品都是素描喜劇。《八十一難》的游戲點(game點)是:《西游記》師徒四人數次達到大雷音寺門口,只完成八十難還差一難;《小品的世界》的游戲點是: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小品,小品中人覺醒了;《史上第一大劫案》的游戲點是:劫匪搶劫銀行,其他人竟然“歡迎打劫”;《年終大獎》的游戲點是:打工人獲得的年終大獎是跟令人討厭的領導一起三亞三日游;《葫蘆兄弟》的游戲點是:如果七娃的葫蘆丟了……

《小品的世界》
觀眾不難從這些節目中發現素描喜劇和傳統的小品的一些本質性不同。
在內容與主題上,傳統小品側重于社會生活、家庭關系等現實題材,通過幽默的方式反映社會現象和人性百態,承載一定的教化功能;素描喜劇的主題則更為多樣和開放,不論是社會熱點、日常瑣事還是經典重構、荒誕想象,都能成為創作的源泉。它追求創意的新奇和視角的獨特,帶有較強的實驗性和探索性。

《葫蘆兄弟》
《小品的世界》就很鮮明地反映出小品與素描喜劇的差別。小品的世界中,爸爸媽媽詮釋的是小品中最常見的主題,叛逆的青春期孩子在父母愛的教化下成長,恩愛的父母因為誤會有矛盾但很快矛盾化解家和萬事興……作為素描喜劇的《小品的世界》則源于腦洞大開的游戲點:小品中的人物覺醒了,他要抗爭……很顯然,這個主題不在傳統小品的選材范圍里。
在結構與節奏上,傳統小品接近于“戲劇”,它有著較為完整的起承轉合,有開頭、發展、高潮和結尾,節奏上側重于情節的連貫性,有一定的鋪墊;素描喜劇不然,往往一開場就直奔主題,迅速拋出“游戲點”,追求快節奏的幽默效果,每個片段可相對獨立,然后不斷升番,馬不停蹄達到高潮,干凈利落地結束。
比如《小品的世界》,開篇很搞笑給觀眾拋出設定;《工作的她》游戲點是對工作的吐槽,由幾個對工作的吐槽片段連綴而成,它不必是一個多么完整的戲劇故事;《史上第一大劫案》,劫匪搶劫銀行,結局不必是劫匪被繩之以法,反而極其荒誕且出其不意……

《史上第一大劫案》
在創作與表演上,傳統小品講究的是一個“打磨”,就像春晚小品幾個月前就開始準備本子,然后編劇和演員不斷打磨,確保劇本嚴謹、表演準確,幾乎不存在什么即興空間。素描喜劇沒這么沉重的包袱,它創作周期較短,創作者可以迅速捕捉社會熱點、流行文化或個人經歷中的幽默元素,將其轉化為笑料豐富的作品,單位時間內能夠產出更多的作品;表演上,素描喜劇鼓勵即興創作和個性化表達,演員須反應快速且具備多變的表演技巧。
唯獨在這一點上,《喜人奇妙夜》并未太鮮明地表現出素描喜劇和小品的不同。這是一檔喜劇競技綜藝,選手們都是犧牲正常作息、花費好幾周時間打磨一個本子,也線下試演過很多次,所有臺詞、反應等基本上也已經成為“肌肉記憶”,幾乎不會在場上臨時發揮。
縱然如此,《喜人奇妙夜》中的素描喜劇還是一定程度上砸掉了“小品的世界”這一堵墻。
曾幾何時,小品是全國觀眾最喜歡的喜劇形態之一,春晚小品常常是春晚關注度最高、最受歡迎的節目,但漸漸地,小品這一范式失去年輕觀眾的喜愛,春晚舞臺上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那種可以反復觀看、一直流傳的經典小品。
小品陷入一定的困境,比如主題的局限性(圍繞家庭關系、職場生活、社會現象打轉),情節的模式化(“喜頭悲尾”),人物性格的刻板化(愚笨卻善良的老實人、聰明機智的騙子、嚴厲的上司、慈愛的母親等),語言的套路化(口頭禪、方言、諧音、押韻、俏皮話等),表演風格的雷同化(依賴程式化、略帶夸張的肢體動作和表情來傳遞幽默)……
《喜人奇妙夜》的素描喜劇,選材豐富、腦洞大開、打破常規、挑戰權威,從主題、結構到語言都更為靈活多變;又由于素描喜劇貼近生活、敏銳感知社會情緒、網感十足,它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場景,提煉出具有普遍性的場景和情感,讓觀眾在歡笑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強烈的共鳴。
受歡迎的喜劇作品必須是這個時代的情緒產品,《喜人奇妙夜》的不少作品都做到這一點。
再筑新墻
本以為《喜人奇妙夜》砸掉傳統小品的舊墻,沒有太多條條框框限制,甩開沉重的包袱,喜劇人的創作狀態會輕松一些、快樂一些,至少不用像以前春晚的小品演員那樣,幾個月前開始準備作品,然后長期地處于高壓的狀態下,直到演出結束才能真正松一口氣。
然而,《喜人奇妙夜》讓觀眾反復看到的還是創作人的崩潰和痛苦。何止是失去正常作息,而幾乎是失去了生活。

這幾個詞精準概括了“喜人”的狀態
節目也并不避諱提到,米未是“喜劇地獄”……顯然,節目組并不認為這是一個貶義詞,而是凸顯米未做節目的態度是如此精益求精,喜劇人為了給觀眾帶來笑聲是如此殫精竭慮、是多么地不容易多么地苦情……

節目中的喜劇人均處于高壓狀態中
我相信大部分觀眾對此是買單的,大家會欽佩節目組,欽佩喜劇人。如果節目好笑,高分就值得更高分,如果不那么好笑,打低分都不忍心了——你知道他們有多辛苦嗎?
且慢,喜劇創作只能是如此痛苦的狀態嗎?當喜劇人砸掉小品的舊墻,不正是為了從以前的模式中掙脫出來嗎?當喜劇人選擇素描喜劇,不正是渴望經由它的輕盈、輕便、快速,讓喜劇可以輕松上陣嗎?何以如今的素描喜劇創作,只能走上痛苦的老路?
于是重新回看下《喜人奇妙夜》第一賽段的作品,會發現原來大多數作品并沒有真正走出“小品的世界”,很多作品本質上只是“素描喜劇形態的小品”,最終走上小品創作“痛苦打磨”的老路。

這確實是春晚小品般的工作量
這些年,小品的“喜頭悲尾”遭到諸多批評反思。“喜頭悲尾”是小品一個常見的結構模式:開頭部分營造出輕松、幽默甚至滑稽的氣氛,吸引觀眾的興趣并引發笑聲;在作品的后半段或者結尾,轉向深刻的情感表達或社會議題,觸動觀眾情感或引發觀眾思考,觀眾或感動不已或淚眼朦朧。
“喜頭悲尾”是文藝創作根深蒂固的“文以載道”思維的結果,既體現小品作為藝術形式的娛樂功能,又展現其承載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的一面。當小品千篇一律這一模式,就會導致作品同質化,觀眾審美疲勞,小品失去新鮮感和吸引力。
《喜人奇妙夜》那些備受好評、讓觀眾流淚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采用“喜頭悲尾”的模式。
《八十一難》在結尾升華了主題,看似解構《西游記》,實則與它的精神內核匯流——師徒情深、慈悲為懷、普度眾生、有情有義,好人不該被人騎的新表達也頗具感染力;

這一刻,還是很動人的
《小品的世界》在結尾升華了主題:哪怕砸掉一切,也仍然有一些東西堅如磐石,比如母愛,雖千萬人吾往矣,也有母親在支持你;

也許母親早已覺醒,不論是“裝睡”還是反抗,都是出于母愛
《斷片山》在結尾升華了主題:攀登人生之峰的過程如同推著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甚至小人物“爬山的意義是不是就是大比兜啊”,仍有人鍥而不舍地跨越;

《斷片山》
《回音山谷》在結尾升華了主題:命運往往讓朋友各奔東西,現實總是讓愿望南轅北轍,但是,朋友,我當你一秒朋友,朋友,我當你一世朋友……

《回音山谷》
這些高分作品看哭評委、看哭觀眾、看哭屏幕前的你我。昔日我們看趙本山、趙麗蓉、宋丹丹等人的小品多數時候不是以哭收尾,我們看《喜人奇妙夜》的作品反而流下更多的淚水。
它們是不是好作品?是!但是,這些好作品代表著素描喜劇應該追隨的唯一創作方向嗎?恐怕要打一個問號。這些作品更像是“素描喜劇形態的小品”,它們“喜頭悲尾”,文以載道,總會在結尾安排一個普適性的情感內核準備擊中我們,等待著我們的淚水;它們需要很長時間的準備,需要反復打磨,需要重復的表演排練,需要犧牲睡眠和生活,需要喜劇人支付痛苦的代價……這一切,都太“小品”了。

《喜人奇妙夜》本身,仍然很“小品”
馬東在接受毒眸采訪時說:“觀眾對于喜劇的需求始終旺盛,這種需求并未因為短視頻和短劇的出現而發生變化。這個需求比我們想的要大,所有做喜劇的人都像在精衛填海。”
當前喜劇市場的矛盾是,觀眾日益增長的高質量、多元化喜劇需求,與市場上優質原創喜劇內容供應不足、創新乏力之間的矛盾。《喜人奇妙夜》將自身定位為“精衛填海”,凸顯了節目組苦行般的努力與付出,確實彰顯了節目的精品化努力;然而,從行業的視角來看,喜劇創作不該只是集中行業主要精力痛苦地去打磨少數作品,精衛填海只是滄海一粟。
誠然,創作者反復打磨、確保每一個笑點都能準確無誤地傳達給觀眾,是保證作品質量的有效手段,但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也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常常會令創作者感到疲憊和挫敗,這也許不是良性的、持久的創作狀態。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不該讓喜劇人將大部分精力用于痛苦地打磨少數作品,不是說不該追求精品,也不是說喜劇作品不值得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打磨,而是喜劇創作不該只有這么一個路徑,喜劇創作存在多元化可能性。既然《喜人奇妙夜》凸顯出素描喜劇,那何不更本質地去體現素描喜劇的創作特點?靈活,輕便,天馬行空,明快,即興,可以沒有什么內涵僅是讓人沒心沒肺發笑,更關鍵是它能夠大量生產。這不僅能減輕創作者的壓力,也能讓喜劇作品更加貼近時代脈搏,更好更快滿足觀眾需求——不是一年一度,甚至兩年一度,而能像《周六夜現場》那樣每周見。
節目組和喜劇人都可以更松弛一些。希望節目能夠推出一些更小體量、更輕便、更快捷的喜劇產品,而非砸掉舊墻后,重筑一堵“素描喜劇形態的小品”的新墻,在觀眾的呼聲和淚水中迷失并走回小品的老路。喜劇人如果能夠更快樂地創作、更高效地為觀眾輸送快樂,觀眾也會更快樂。